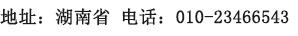撰文/JürgenTautz摄影/IngoArndt
昆虫、啮齿动物以及鸟类的创作是一件件艺术品,它们造型奇特,线条优美,实用性强。
只是,这些艺术品通常只存在于黑暗不起眼的角落里。那么它们的意义何在?大多是用来对抗天气的变化以及敌人的威胁。
建筑知识又是怎么得到的呢?是从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收集来的。筑造用的什么材料?全部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
这件作品呈球形,大小与网球相似,由许多极细的植物叶茎互相交错编织而成。它被仔细地固定在几枝杆茎间,悬于地面之上,偶尔也会随着植物轻轻晃动。是哪种鸟筑造了这样一个羽毛般轻巧的巢?不是鸟,而是老鼠!
简直不可思议;这违背了牛顿和他的万有引力定律。是老鼠新长出了翅膀吗?它们什么时候学会了这种编织流苏花边的手法?
就是这群长约七厘米长,重量只有五克左右的巢鼠设计完成了这件大师级作品。在它们的后代降生前十天左右,巢鼠夫妇就要开始忙活起来了。它们一般选取较硬的植物,比如农田作物或者芦苇的杆茎,用来攀缘和筑巢。
筑一个巢需要用掉差不多两百条植物杆茎。这些杆茎被均匀地撕成细条状并在末端被编织在一起。鼠巢上部被固定在植物杆茎较高的位置,并由重力拉弯作物杆茎在空中保持住平衡。住在半空中对于巢鼠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区时常会受到洪水威胁。
就地取材的天才种族动物的建筑艺术属于进化史中最迷人也是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一部分。它们的作品不仅符合我们考究的美学标准,同样也发人深思:在追寻生存的意义的整个过程里,我们只是万千物种中平凡的一员。
而生存的意义对人类以及动物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保证自身得以存活,同时也能保证后代的繁衍。
自然界中各种新奇的生存方式便不胜枚举,在地面和水面都可以找到朝上或者朝下、修筑得五花八门的巢穴,它们或是轻巧或是沉重,造型优雅实用,却完全不需要挖土机,起重机或是水泥搅拌车的帮助。
建筑的材料都是什么?通常都是就地取材地将各种东西混在一起使用。马蜂群会把木质纤维咬碎,再将其吐出,并与唾液混合,用以筑成纸质巢穴。燕子们则像制陶工一样用小粘土块筑巢。蚂蚁会口含幼虫,像使用胶棒一样,迫使其在叶缝或枝条间吐丝,从而缀合、粘牢而成为蚁巢。
澳大利亚织工蚁有着惊人的团队合作能力:在筑巢时,这群建筑师们会首先达成一致,一起拖拽叶片的某个位置。其他一些工蚁则会用上颚和腿按蚁巢的大致形状将叶片固定起来。另一群工蚁便会小心翼翼地用一种特殊的粘合剂将叶片的缝隙粘合在一起。这种粘合剂就是工蚁幼虫吐出的丝。
有时,它们修筑的是只需要用一季的临时巢穴。有时,上百万个建筑大师需要通过严格有组织的分工合作,才能倾力打造出一座可以维持百年之久的建筑作品。为了完成这样的作品,按照人类的经验,谨慎,细致的计划以及相互协作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在惊叹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些疑问:
是什么促使这类动物去筑巢,而剩下的大部分却并不需要?
它们对自己所筑巢穴的实用性以及美观性有多少了解?
人们可以从它们身上获得什么启发,得到哪些创新的想法?
建筑无关智力一件无可争议的事实摆在面前:先有建筑作品,然后才是大脑。迈克-汉赛尔(MikeHansell),一位来自于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教授,将他的整个科研生涯都贡献给了关于动物建筑艺术的研究。
他拿一种学名difflugiacoronatade的阿米巴虫举例。阿米巴虫是一种单细胞生物,生活在水中并且大概只有1/微米。只有通过高倍显微镜观察,才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生物进化赋予了阿米巴虫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它们可以自己筑造一座由沙粒构成,可以背在身上移动居所。
阿米巴虫通过细胞分裂来繁衍后代。每只阿米巴虫都背着一个可移动“城堡”。没人知道它们是从哪里、如何获得的这个城堡的“建筑专利”。它们具体是怎样带着“城堡”分裂繁衍的,只有通过仔细的观察才能得到答案。
这个单细胞生物会在进食的时候吃下一些“建房”所需的但是难以消化的微小沙粒。这些沙粒会先停留聚集在它的体内。直到繁殖的那天,细胞分裂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和平离婚:两只变形虫中的一只会获得这个专属“城堡”,而另一只则需要重新再去建造一个。重建“城堡”时,在体内积攒已久的沙粒堆会慢慢地先移动到皮肤边缘,然后再隆起形成一座新的城堡。
在澳大利亚北部,指南针白蚁修筑的巢穴按照南北方向精确地排成一列。所以当正午太阳高度角最大也是全天气温最高的时候,阳光只能照到这个约有三米高的蚁穴的侧面。再配上设计巧妙的空气流通技术,蚁穴内部就可以一直保持着让白蚁们最舒适的温度。蚁穴的这种指南针技术不过是白蚁所创造的众多建筑专利中的一个。其余还有例如六米高的烟囱式的蚁穴尖顶以及穴内温度调节技术。
科学家们想通过一个简单的试验来说明昆虫的应变能力以及灵活性——它们懂得利用现有的巢穴。研究人员通过细微调整周围环境,为一群六只脚的昆虫们提供了新的庇护所,同时也给它们设置了新的机遇与风险。
园掌舟蛾的幼虫以几乎所有的带有绿叶的植物为食:桦树,山毛榉,橡树,赤杨树,金链花,菩提树,杨树,榆树,柳树以及一些蔷薇灌木。有时候,这些贪得无厌的幼虫会将树木啃得连片叶子都不剩。有些情况下,它们会事先织出一张丝网,罩住那段它们准备食用或者用来休息的枝叶。一旦这个丝网内的叶子被全部吃光,它们就会重新织网罩住新的枝叶,为下一次的饕餮盛宴做准备。但这种情况并不非常常见。
在实验中,科学家们将杨树枝上的叶片小心翼翼地卷起来(注:许多昆虫和蜘蛛会将植物叶片卷起作为自己的庇护所),并用回形针把叶片全部固定成圈状。
作为对比,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普通的未被变动过的杨树叶。在一段时间的实验观察后,科学家们通过对比被回形针固定过的杨树叶和未被卷起的杨树叶得出结论:在事先固定好形状的叶片卷上的昆虫数量是未被改变形状叶片上昆虫数量的七倍之多,而且种类也要比后者多出三倍。
在这个由回形针固定出来的微型生态系统中,既有以叶片为食的昆虫,又有专门猎食这类食草昆虫的肉食昆虫。因此,汉塞尔教授得出结论:生存环境越复杂,生物多样性就越丰富。
生物体不仅会根据所处的环境来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同时,它们也会尝试着不断改变身边的环境使其更利于自身生存。
巢穴筑造的创新虽然不是唯一一种适应环境的方法,但却是征服全新生存环境的一种理想方式。
如果你认为,动物只能建造出朴实简陋的巢穴,那就大错特错了。枝头高歌的鸟儿会告诉你,在动物界同样存在着令人惊叹的华丽建筑作品。暂且来听听它们这首关于筑巢的颂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