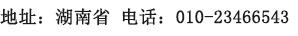一般杂花图是以横幅为主,依次画出不同季节、不同种类的花卉,但是徐渭画的却是巨幅竖轴的,而且两幅杂花图非常相像。其中一幅为《十六花姨图》,纵.7厘米,横99.1厘米,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另一幅是《花竹图》,纵.6厘米,横.5厘米,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专家分析,《十六花姨图》是徐渭的真作而《花竹图》是摹本,理由是落款文字有几处不一样,画面也有几处不同。我倒是觉得有可能两幅都是真迹(个人猜测),理由是既然要临摹一般是原样照搬,不会存在那么明显的差异等待后人诟病,况且古人常以“以假乱真”为荣。
徐渭《花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六花姨图》是高逾三米的花鸟画巨制。文人画大多擅长以花喻人抒发心绪与情感,而“十六花姨”偏偏反其道“以人喻花”,可见徐渭处处异于常人。画中巧妙穿插安排梅、兰、菊、竹、芭蕉、牡丹、水仙、荷花、秋海棠、茶花、芙蓉、秋葵、石榴、萱花、绣球花、玉簪花共十六种花木,将四时花卉集于一轴而毫无违和感。《十六花姨图》给人时空交错的联想,表现出画家驾驭冗繁主题的超强能力,也证明了花鸟画亦能发挥出高大上的磅礴气势,一点不输山水画。
两幅画都是没骨写意加双钩,书法运笔,水墨尽兴,大笔泼墨石面与叶子,双钩白描画竹钩花,画花笔法迅捷恣肆,晕染时水墨流动,墨色层次变化丰富,画面生动热闹。很显然画家对笔情墨趣的表达要比精细描绘景物更感兴趣,但是描写花卉也是粗中有细,笔法变化丰富莫测。
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两幅画对比强弱之势斐然,用笔用墨都有很大的差异。简单地举几个例子,就拿两幅画的细节比较(左为《十六花姨图》,右为《花竹图》),首先《花姨图》的竹子之竹节处起笔是有明显变化的,双钩的线条也是有粗细浓淡变化的,而《花竹图》却几乎看不出变化,意思是线条几乎雷同。
其二,兰草与假山石的关系处理上,《花姨图》明显轻松爽快,而《花竹图》却显得吃力和刻意。
其三,《花姨图》中的假山石是先用淡墨铺底,再用重墨破淡墨的,而《花竹图》中的假山石却是用中墨侧缝排出墨块,二次补重墨,有的边沿也是二次中墨勾勒轮廓的。
其四,凸起的地面,《花姨图》中是用淡墨泼墨,自然,随意性强;而《花竹图》中还是与假山石同样的方法,是用侧缝刷出平行的墨块。不算说哪种就不好,而是想表达:当时明代的泼墨画法“流行”《花姨图》中那样的,徐渭也是。
凡此种种分析下来,我也开始赞同专家的结论了,《花姨图》更像是徐渭的亲笔真迹,《花竹图》可能是复本。
《十六花姨图》画右自题“余画十六种花”,“因怀徐陵杂曲二八年时不忧度,自作一歌,因为‘十六花姨歌舞……’”,落款“天池道人渭”,既道明此画题来意,又可谓书画相得益彰,此画堪称是徐渭存世大写意花卉中最为难得的佳作。
有人形容徐渭的泼墨大写意是“不见物象,满纸墨影”,我觉得是“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徐渭把花鸟画中的“文人墨戏”飙到了新的高度。
(注: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不妥,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