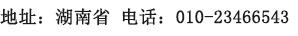外婆家门前那条大河是我和小伙伴童年的秘密基地,从家门前先走到镇中学,再从后门穿过一条狭窄的小路就到了。我怕水,总是在河边呆呆地坐着,看比我大的哥哥们穿着短裤站在岸边的石头上纵身一跃,溅起巨大的水花,溅到我的白色裙子和我的粉红帽子上,让炎热的夏天多了不少清凉。我对夏天从三岁开始就有了记忆。十六岁那年和妈妈一起见她在厦门的好朋友陈阿姨,陈阿姨一直说十几年前去安徽找妈妈玩时的情景:“你们那里的房子做的好漂亮!一排排,都是白白的!”我很想说我也记得,但不知从何说起。记忆中从出生到我初中毕业的所有夏天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夏天有舅舅从地里挖出来的菜瓜,切成片,撒一些白糖,拌一拌就可以直接吃,那是泥土本身的味道,带着乡村的淳朴被我一口口吞下,让我也变得纯粹起来。
这张照片的确是我三岁那年陈阿姨帮我和妈妈拍的,那时我和妈妈的关系还很好,她极力照顾我,放弃自己在异地小有成就的事业,回到家乡,回到我和爸爸身边。陈阿姨是她在异地最好的朋友,当她们都在过自己的生活时,彼此就成了彼此唯一的精神食粮。陈阿姨生活在海边的小岛上,平日里与外界隔绝,孩子和丈夫都十分人让人省心,我想可能唯一放不下的是自己。我长大以后经常会偷听到妈妈和陈阿姨的电话,聊天内容除了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更多的是人生,或者说对于自己已经度过了的人生的不甘与悔恨。我想每个人都有过这个阶段,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如果一个人还在坚持和朋友讨论自己的人生与曾经的抱负,我认为她一定是一个浪漫的人。我喜欢浪漫,喜欢在从海边飞到河边看望朋友的陈阿姨,喜欢单纯的友谊和她们在双人床上的黑夜幻想。
这张照片上的我呆呆的,嘴角向下,眼睛眯眯的;戴一顶白色帽子,帽子里似乎是个小光头,穿着一条带着棕色斑点的白色连衣裙,这种连衣裙我长大以后再没穿过;脚上一双白色凉鞋,可能是妈妈为了搭配我的裙子和帽子才给我穿上的。妈妈那时也是短发,当然她现在也是,我印象中她有过长发的日子,还在理发店把头发拉得笔直,整个人都变得刻板起来。那段日子也是刻板的,生活似乎非但越来越不浪漫,还越来越清苦。越是苦,大人们越是不会苦中作乐,只是连同自己的外貌和发型都变成一脸苦相的样子,仿佛这样能把生活的苦释放出来。照片中的妈妈二十五六岁,做妈妈已经有三年了,这三年里她一定很累,离开了熟悉没多久的城市,离开了最好的朋友,也离开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更离开了物质与财富。一切都得从头再来。我有时想,人为什么会对人产生“他很伟大”的印象,因为爱?因为无法控制的私欲?还是因为对另一个人的同情和眼泪?或许都是,也或许都不是。我相信妈妈是因为爱,因为年轻的我对爱情充满期待。
十九岁这年再看这张照片,好像变了很多,又好像没变:身后那条河还是那条河,过年的时候心血来潮去望望,河水还是很清澈,有人蹲在石头上拿着棒槌洗衣服;妈妈还是短发,只不过发型比十六年前好看,而且由于白头发太多经常在家自己用染发剂染色;陈阿姨前两天还和妈妈通过话,大抵是在数落老天爷对自己的不公,那些不公平的点点滴滴伴随着呜咽声通过无线从海的那头传到山的这头,妈妈心疼,说过段时间一定要去看看她。改变最多的是我吧,我很少和妈妈一起拍照,也很少让她帮我拍照了,原因是我嫌弃她的拍照技术太差。我有时觉得自己真的长大了,不仅是年龄上的长大,更多的是我自认为我拥有了独立的人格,以及为人处世时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原则。可有时候我又觉得我并没有长大,我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很多种感情没有体会过,我还没有走到“听妈妈的话”的阶段,我还是太故作独立了,故作独立的人有时就是叛逆,就是长不大的孩子,就是固步自封地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人间所有的法则。这挺天真的。
总而言之,感谢母亲赐我有关文学的天分,更感谢她给我机会,做我想做的事,写我想写的文章,描述我所体会的生活——我的生活来源于乡村,来源于一切带有泥土气息的大地。
谢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